理髮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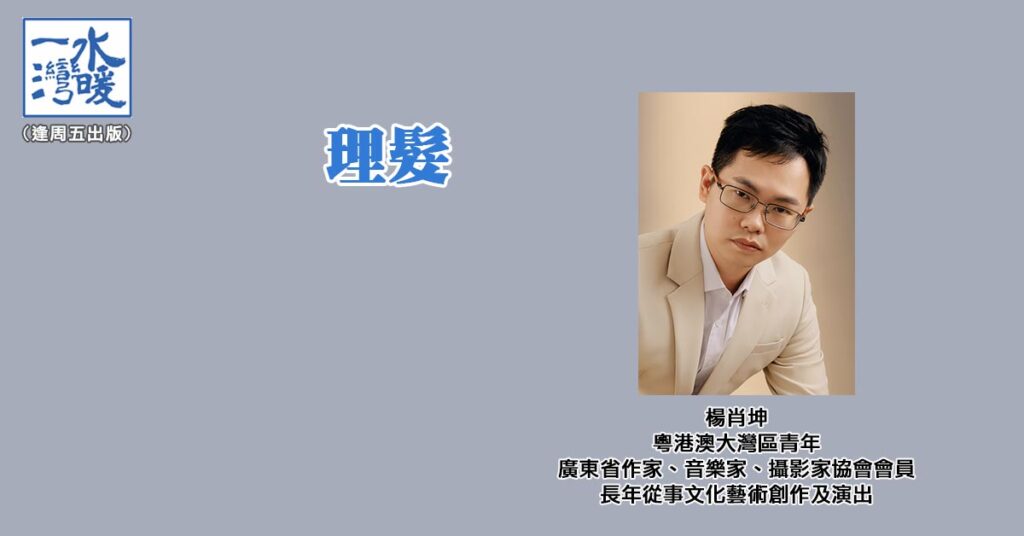
剪了頭髮的小女兒咧嘴微笑,操著還不算太穩的腳步向我走來,一眼看去活像一個小男孩。「哇,你好靚仔,好似爸爸小時候呢!」我笑道,然後又問,「找二伯剪的嗎?」「是啊,二伯剪得可好了。」父親說。
自我朦朦朧朧懂事起,二伯就是一位理髮師。他與理髮打了大半輩子交道,先是任職於理髮社,後來理髮社結業了,又自己開了家小理髮店,繼續服務街坊。在我三十多年的印象裏,他的確沒有投身過別的行業,似乎就是上班給客人理髮,回來了還常常剪不離手,家族裏幾乎找不出哪位的頭髮跟二伯的剪刀沒產生過交集。理髮是不是他的理想職業,我不清楚,我只知道那把剪刀和那份手藝,都傳承於爺爺。據說曾祖父也是手持理髮剪刀的,日本侵華期間,有一次家裏實在是揭不開鍋了,曾祖父還叫尚為少年的爺爺把剪刀當了換買食物。後來,爺爺離鄉別井,幾經輾轉回到家鄉娶妻生子,離不開的始終是一把理髮剪刀。據說,那時候粵劇藝術大師紅線女前來演出,爺爺曾兩度為其理髮,成為家族裏的佳話。
我自出生起便開始享受這「明星級」待遇,直到初中,頭髮基本都「逃不過」爺爺的「料理」。坐上椅子,上衣一脫,雪白的理髮袍立刻在奶奶的手中飛舞而過蓋在身上,猶如一襲換了方向的披風。這時,全金屬打造的剪刀、碎髮刀、髮鏟開始輪番上陣,一片習習聲中,那些被認為不合時宜的頭髮便紛紛散落在袍上、地上,當然還有不少會粘在我的脖子,或是爺爺的手上。「得啦!」隨著爺爺一聲號令,奶奶就伸手解開袍子,領著我去沖涼房,蹲到已事先備好的一盆水前,把頭髮洗乾淨,再用老式電風筒吹幹,真是名副其實的「洗剪吹」一條龍服務。
然而,對那時的我而言,每次理髮其實都是一個戰戰兢兢的過程,尖銳的金屬聲讓人發抖,冷冰冰的利器仿佛隨時就會誤傷到細嫩的皮膚,還要這樣乖乖地端坐十幾分鐘,實在不好忍受。當然,換位思考,給孫子們理髮,爺爺也頗有微詞,「坐唔定」就是他最常用的批評,有時甚至搬出舊時代的一套說辭,「放在以前,是把你的頭按下去再剪呢!」到了二伯那裏,言辭固然溫柔些許,但當那套金屬裝備在自己頭上肆意舞動時,心裏依然感到不安。因此,理髮在我眼裏,一直不是什麼好事物,幾乎到了可免則免的地步。
長大後,我逐漸把理髮交給外面的髮型屋,最早是樓下一家叫「彩虹髮屋」的小店,門口掛著的紅白藍三色燈轉個不停。在那裏,我才知道原來理髮剪可以只如掌心般大小,刀鋒摩擦時發出的聲音也溫柔許多。於是,理髮這個事情,自然而然地就變得可愛起來。到了大學時代,理髮的足跡便開始遍佈學校附近的品牌機構,從口碑和價錢上作出權衡,也常常沒有固定的髮型師。這時,我對理髮的感覺變得又愛又怕,把頭髮委託給一位陌生人,就如坐過山車般刺激,髮型的好壞全憑運氣。許多年過去了,不知是理髮師的水準得到普遍提高,還是我對世事已多少有些看淡,似乎只要打開門營業,理髮師的技術都妥妥線上,只需一句「剪得自然一點」,就准不出意外。至於近些年開始流行的男士剪髮,倒是一直沒有嘗試,一來價格偏高,二來擔心自己毫不突出的五官和臉龐輪廓襯不上挺立風格的髮型。三來嘛,那種店裏的髮型師好像總是紋身抽煙甚至帶鼻環的,與自己風格相去甚遠。今年早些日子,家裏附近還開了一家僅有一名理髮師且無需洗髮工的店,主打AI洗頭,不禁讓人聯想,不久的將來,理髮師也被AI所取代。
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,周圍的一切仿佛都在飛速變化,相對來說,理髮作為傳統服務業,確實已經屬於在原來面貌上保留得比較完整的,大部分無非是在附加值上做文章。當然,有的人更為念舊,譬如我爸,還是喜歡找二伯剪髮;又譬如已在佛山紮根數十年的大伯,依然使用著爺爺留給他的老式電風筒,哪怕它的吹髮效率近乎老爺車,也絲毫不減大伯的堅持。 此刻,我不自覺地摸摸自己的腦袋。嗯,頭髮還短著,距離下次理髮,估計是一個月之後吧!
作者:楊肖坤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,廣東省作家、音樂家、攝影家協會會員,長年從事文化藝術創作及演出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