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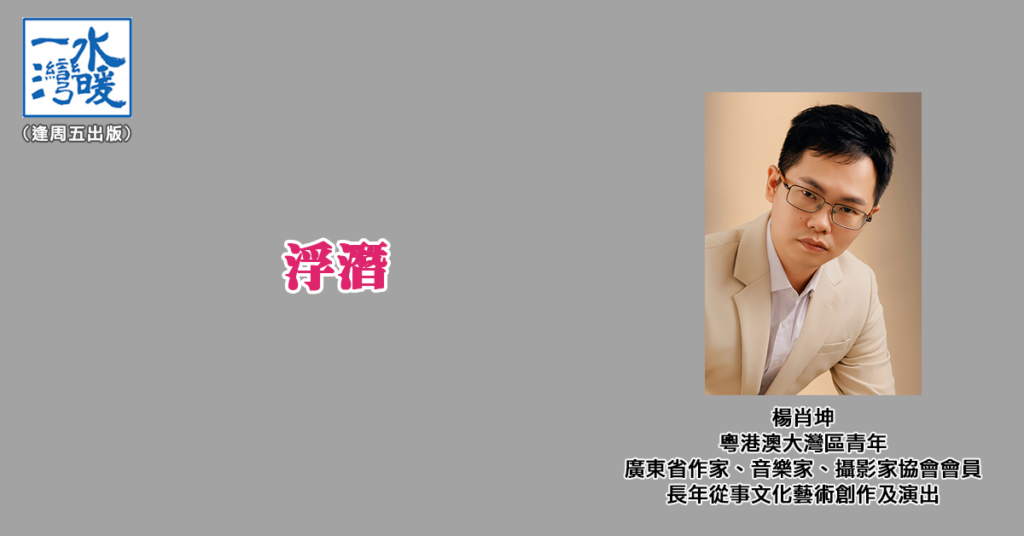
一場暴雨傾盆而至,仿佛比高溫更有資格向人們訴說——2025年的夏天,真的來臨了。光陰似箭,今年不知不覺已走過了三分之一,如果要用幾個關鍵字來定義這一百二十多天的話,此刻我首先想到的,是當代藝術。
春夏交接之際一個陽光明媚的週六下午,我與孟儒紹(Ruscha)來到開平塘口的天下糧倉先鋒書店,共赴一場簡約的當代藝術盛宴——從英國遠渡重洋歸來故土的藝術家李典宇老師,以「回到祖屋的月光」為題,分享他用攝影和複合型行為的方式,與年邁的老母親共同完成一次當代藝術探索。而在此兩周前,Ruscha主營的L-1當代藝術畫廊也正好迎來了全新的中畫幅雙人攝影展「夢中雙城」:從喀什到尼羅河畔。在Ruscha眼裡,這是一次「以當代藝術的棱鏡,結構旅行者帶回的視覺標本」的過程,「是一場關於縈繞在旅者腦海中的夢境,也是兩地文明層積的視覺思辨:當旅行者的私人記憶經過膠片等方式的輸出,得以窺見人類文明如何在遷徙與碰撞中,將異質性的碎片熔鑄成流動的史詩」。
我倆坐在三號倉的階梯上,圓柱體的糧倉讓李老師的話語如焦點般散射到每一位聽者身上,形成一個扇形。他提及自己生於廣東臺山,童年時跟著家人輾轉香港,長大後遠渡英國,並在那裡成為了一名大學教師和藝術家。他進而談起重病過後的母親,和那場行為藝術。白髮蒼蒼,臉上滿是皺褶的老母親飾演著掛在樹上的蝙蝠,兩個圓形構圖的鏡頭分別鎖住了她的模樣,投射在漆黑的畫面上,仿佛那是穿過望遠鏡所定格的瞬間。「我母親的枕頭底下壓著外婆的照片,但我從來沒聽到過她的聲音。」於是,李老師回到臺山祖屋,開始了一場尋聲之旅。祖屋日久失修,夜晚,月光從屋頂的破洞中穿透而過,落在地上。李老師把外婆的照片以四十五度角的姿態擺在月光之下,又在照片旁邊放置一個聲音裝置——那是一個他專門找朋友訂做的藝術裝置,可以讓光線轉化為聲音,估計是來自某種光敏元件和電波的作用。月光通過照片產生折射,隨即進入裝置,化作電波聲響。據說電波斷斷續續,間或還出現留白。「這是非常自然的」,李老師說,「就像我們寫作時的停頓與斷行。」講座之後,我和Ruscha在塘口村邊走邊聊,就當代藝術交換想法。他不時拿起隨身攜帶的小型相機,用快門記錄有趣的畫面。他向我推薦三本學習當代攝影的書籍,而這次推薦竟也讓他自己顫動起來奮筆疾書,一周後發佈文章《難怪你看不懂當代攝影!因為你沒讀這三本書》。
不久後,我收到羅行藝術墟策劃總監柳莎的消息,關於北江吾舞國際舞蹈節。5月2日下午,我帶著家人應約奔赴南海羅行,在夜幕下目睹了當代舞蹈在駐地藝術中的更多可能性。村道、窄巷、草坪皆為舞臺,在那些肆意扭動的肢體語言中,我感受到從舞者身體中迸發而出、意欲劃破黑夜的力量,一種情感形而上的遺痕。是的,舞臺從不被具體空間所定義,只要擁有肢體,舞蹈就不會消失。
五一假期過後,我開始參加廣東省作家協會的第四期「作家活動周」。報到後,在黃昏降臨之前,我來到廣州藝術博物院,走進命名為「時間的新劇場」的首屆灣區當代雙年展。那一刻,外面密佈的烏雲肆意地打濕了整座城市,而人影寥寥的劇場內,時間仿佛成了一塊切片進而得以凝固下來,讓人不禁環顧思考,四周幾近光怪陸離的藝術裝置,是如何從社會歷史、藝術語言、全球語境和未來想像的角度,縱橫交錯地探討當代藝術所關注的新現實乃至未來史。
當代藝術是一個動態的過程,隨著社會運轉時刻處於變化狀態,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固定樣式。誠然,對於當代藝術,我涉獵尚淺,實在沒有話語權可談。但是,我更願意視之為一種「浮潛」——遠遠沒有觸及深處,卻至少可以在當代藝術的浩瀚海洋中漂浮、下潛、上升、呼吸,感受身體與海水在互動中彼此構建的關係。
在生活中撕扯,在探索裡浮潛。也許,這正是自己當下的注腳吧。
作者:楊肖坤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,廣東省作家、音樂家、攝影家協會會員,長年從事文化藝術創作及演出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