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種活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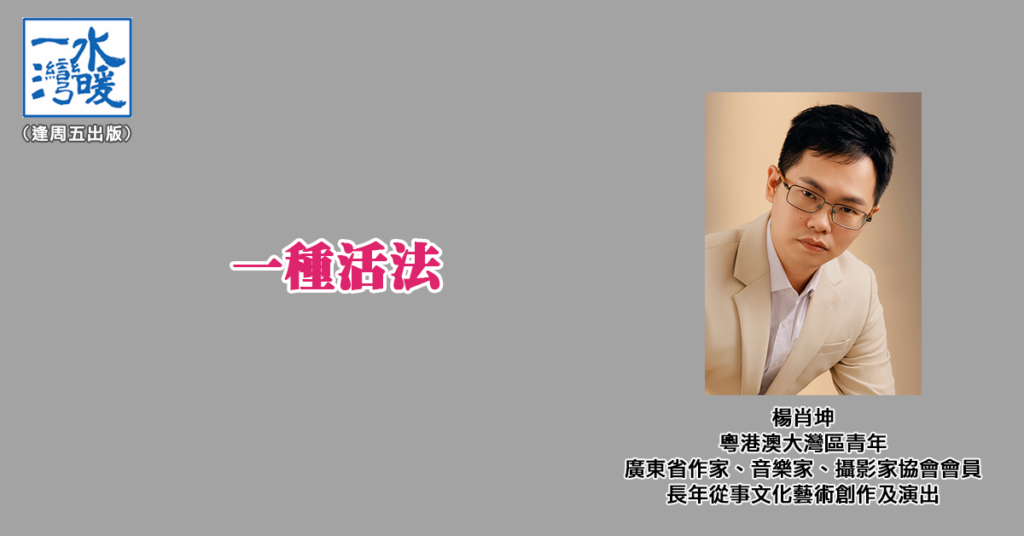
得知開平玲瓏村迎來首位百歲壽星的消息,已是夜深時分。記得十三年前,也是一個夏日的深夜,我坐在玲瓏醫院董院長的國產皮卡後排,從市區向著玲瓏村出發。三十出頭的董院長有著一副微胖體格,加上慈眉善目的樣子,仿佛天然自帶著「距離消除器」。副駕駛座上坐著他的醫生太太,那時兩人在玲瓏醫院任職已將近十年。
董院長為我在玲瓏醫院安排了宿舍。宿舍周邊萬籟俱寂,那一夜我睡得頗為踏實。第二天陽光明媚,我跟著董醫生到玲瓏村逐戶走訪,眼前的身體殘缺與變形,雖然已不再陌生,但悲憫之情依然不經意間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淹沒心頭。
公元前1550年,古埃及《埃伯斯紙草書》首次記載類似麻風病的症狀,而在中國,據說麻風病的記載可追溯到殷商時期。《黃帝內經》曾稱麻風病病症為「鼻柱壞而色敗,皮膚瘍潰」,明代《普濟方》則直接以「五死」來描述病症從皮肉到筋骨血脈之恐怖——「皮死,遍身麻木不治;肉死,刺割不痛不治;筋死,手脂脫落不治;骨死,鼻樑崩塌不治;血死,潰腓成膿不治」。
第一次被麻風病所震驚,是在2012年。那一刻,我眼前所見之狀,與古籍所記如出一轍。那天,我跟隨朋友到臺山參觀攝影展,主題關於臺山大襟島麻風病康復者的遷徙。方寸之間,如一塊塊拼圖,構建起鏡頭內的麻風病康復者世界。這個世界,從某種程度來說,是與我們隔離的。隔離,固然是抵抗病毒傳染之必要,但縱使得益於現代醫學的他們已擊退病魔,「麻風病康復者」的標籤仿佛依然是「惡魔」的代名詞,讓人退避三舍。於是,曾以為可以重歸家庭的他們,在家人的冷漠中,在社會的歧視中,又或在自尊自卑的相互纏繞中,選擇了留在原地,抱團取暖。那裏沒有「別人」,就算面容軀體的殘缺並不相同,言行習慣也各有個性,但彼此平等,也無需忍受他者的冷眼閑言。更何況,醫生護士的照料,基督教團體的幫扶,於其又何嘗不是晚年生活的恩賜?當一切順理成章,一種活法也就隨之形成。
照片講述著麻風病康復者的日常生活,又記錄了他們離開這個已視之為家的孤島的幾個瞬間。我流連其中,遇見了作為攝影者之一的鋒哥。鋒哥是七零後,沉迷於黑白菲林相機與人文攝影。厚重的主題,敬畏的快門,黑白的呈現,在他眼裏,這是一種相互匹配,也是一種關於攝影的活法。同為攝影人,我很快就與他搭上話題,還互換了聯繫方式。
不久後的五一假期,我在佛山坐上鋒哥的陸風越野車,直奔東莞的泗安醫院。那也是一家收容麻風病康復者的醫院,安置了一批從大襟島遷離的老人。一張張曾在照片裏認識的面孔,此刻相繼抵達視線。我跟他們聊天,他們對舉起的鏡頭也毫無拒意。吃飯,散步,閒聊,對於基本生活,他們與常人幾乎無異,那些肢體困難也早已克服——更準確地說,是經已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他們幾乎每戶都放著耶穌、聖母或十字架,基督教對麻風病群體的救濟,從羅馬帝國晚期一直延續至今。
依靠鋒哥帶來的帳篷,我在泗安醫院的草坪上度過了兩個清朗的夜晚,在天色初白之際醒來。拉開帳篷拉鏈,已見一些尚有勞動力的麻風病康復者在參與勞作。他們會笑著向我打招呼,熱情甚至比醫院長期駐守的志願者還要高漲。
最後一天適逢禮拜,一位神父披掛入戶,給老人們喂上一片硬幣般的白色食品,然後將手掌輕輕置於其頭上進行祈禱。走訪完畢後,大家又跟著他來到小教堂,禮拜的氣息溢滿整個空間。有人告訴我,這個是天主教教堂,而對面的教堂屬於基督教。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流派之一,在歷史演變中,有了各自的信徒。那個下午,醫院迎來了一批大學生志願者,其中一位男生叫大亮。我和大亮一行走入一位康復老漢的家中,一幅貼在牆邊,用紅色筆勾勒而成的日式少女風漫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。老漢說,曾有一個日本團體過來慰問,這是其中一位女生送給他的。「當時她為日本侵華向我懺悔,老漢邊說邊模仿女生雙手合十低頭的姿態,「我告訴她,不關你們的事,是前人犯的錯。」我留意到,那幅畫的一角留有畫者名字,用字母寫著「Sakura」。
那天之後,便有了我走進開平玲瓏醫院和新會蒼山醫院,見證不同麻風病康復者群體的經歷。異於常人,卻又如常活著,他們已然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活法。選擇投身麻風病康復事業的董院長夫婦,拿起相機記錄麻風病康復者的鋒哥,還有那些來自不同五湖四海的宗教人士或志願者,他們的選擇,則又是一種活法。活法,是執著與變通經過漫長的相互撕扯後取得的和解,終究就是一種自洽,一種平衡。
消息顯示,玲瓏村那位百歲壽星名叫梁如旺。照片中的他身板硬朗,陽光照在臉上映襯出一臉平和。他凝視著一個繡著福字的大同心結,燦爛的紅,與健康的梁老相映生輝。在玲瓏村時,我見過他嗎?我無法拿出確切答案,但我相信,彼此有過交集,就像那無數個他,正向我發出活法的啟迪。
作者:楊肖坤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,廣東省作家、音樂家、攝影家協會會員,長年從事文化藝術創作及演出

